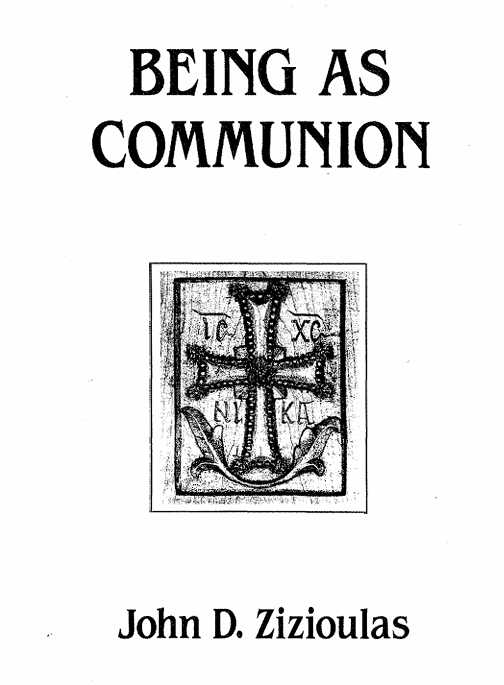今天睡前继续读《存有作为交通》的简介部分,做个简单的记录
在教父时期,极少关注教会的存有(there was scarcely mention of the being of the Church),大量的辩论和思考都在上帝的存有上(whilst much was made of the being of God)。在那个年代,出生自带的配置就是有神论,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,从来不会为神存在与否而争论。那争论什么呢?原来争论的是上帝如何存在。(how he existed)因为这个问题会牵涉到教会和人类,因为教会和人都带有上帝的形象(images of God)。
就像泛神论者有他的上帝观,一神论者有他的上帝观,多神论者也有。那么教父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,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各种上帝观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希腊的上帝观。
而希腊上帝观是根植于他的本体论,一种根深蒂固的一元论(Greek ontology which was fundamentally monistic)。这种观念认为上帝和这个世界是联合的,是不可分割的整体(the be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being of God formed, for the ancient Greeks, an unbreakable unity.)。这种观念与圣经所宣告的上帝相对世界是全然自由的,有根本性的矛盾。
所以教父们所做的应该不是调和希腊哲学与圣经,而是要拆毁重建。柏拉图的造物主观念(The Platonic conception of the creator God)限制了上帝的绝对自由,因为这观念是基于物质先存的信念而来,实际是趋于唯物主义的。所以,必须要建立新的本体论来超越希腊式的一元论本体论的禁锢。
在那个时代,还有一个巨大的敌人,就是诺斯底主义(gnostic systems)。此观念则认为上帝与世界之间有巨大的鸿沟(gulf),是不可跨越的。因此,教父们在面对这两个思想劲敌中,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本体论,应该是那个刀光剑影的岁月中留存的最为卓越的果子。
新型的本体论是如何创立的呢?齐齐乌拉斯说了那时出现的两条建立路径,一条称之为学术型路径,另外一条称之为教牧型路径。
走学术型路径的教父们,都是学者型神学家(academic theologians),如殉道者游斯丁、亚历山大的革利免、俄利根等。他们主要关注基督教的启示(revelation)层面,所以更多操作的智性训练,如各种哲学思辨。这条路径未能摆脱希腊思想中的一元本体论陷阱。
走教牧型路径的教父们,都是教牧型神学家(pastoral theologians),如伊格纳修、爱任纽、亚他那修等。他们是透过教会团体(ecclesial community),也就是教会性存有(ecclesial being)中的经验来认知上帝的存有的。
而后面的这个路径,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可操作的本体论,不仅是在智性思辨层面。因教会的共融而体认到:上帝的存有只有透过位格间的关系与爱来认知(the being of God could be known only through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personal love)。也就是,存有意味着生命,而生命意味着共融(Being means life, and life means communion)。
今天就到这里,要睡了。